白话三国——第八十六回 难张温秦宓逞天辩 破曹丕徐盛用火攻
东吴的陆逊在打退魏国军队后,被吴王任命为辅国将军、江陵侯,还负责管理荆州。从此,军权都归陆逊管辖。张昭和顾雍向吴王建议,要求改元。吴王同意了,改为黄武元年。突然收到报告,魏主派使者来,吴王召见了使者。使者说:“蜀国之前向魏国请求救援,魏国一时未能明白,所以派兵应援;现在魏国非常后悔,想要派四路军队去攻打蜀国,东吴可以前来接应。如果能拿下蜀国的土地,可以各分一半。”
吴王听后,无法决定,就问张昭、顾雍等人。张昭说:“陆伯的意见非常有见地,可以问问他。”吴王于是召陆逊来。陆逊说:“曹丕在中原稳守,急不可攻;如果现在不顺应,必然会成为仇敌。我估计魏国和吴国都没有诸葛亮这样的对手。现在先勉强应允,整军准备,只需探听四路军队的情况。如果四路军胜利,蜀中就会危急,诸葛亮前后无法救援,主上就可以派兵应援,先攻打成都,这样是最佳策略;如果四路军失败,再另作商议。”吴王同意了,于是对魏使说:“军需尚未准备,择日再起程。”使者辞别后离去。
吴王派人探听到西方的军队出西平关,见到马超,未战先退;南方的孟获发兵攻打四郡,却被魏延用疑兵计杀退;上庸的孟达在半路上突然生病,无法行军;曹真的军队从阳平关出发,赵子龙守住各个险道,确实是“一将守关,万夫莫开”。曹真在斜谷道驻军,无法获胜而退回。孙权得知这些消息,便对文武百官说:“陆伯说得真对。我贸然行动,反而与西蜀结下仇恨。”这时又收到西蜀派邓芝前来的消息。张昭说:“这是诸葛亮退兵的计策,派邓芝来做说客。”吴王问:“我该如何回应?”张昭说:“在殿前立一个大鼎,放几百斤油,下面用炭火烧。等油煮沸后,挑选身材高大、面宽的武士一千人,各持刀剑,从宫门前直排到殿上,再召邓芝进来。不要等他开口说话,就用郦食其说齐的故事责问他,看看他会如何回答。”
吴王听从了他的意见,立刻准备了油鼎,命武士在两侧站好,各执武器,召邓芝入殿。邓芝整理衣服,走到宫门前,看到两行武士,威风凛凛,各持钢刀、大斧、长戟、短剑,直排到殿上。邓芝明白他们的意图,但并不害怕,昂首走上前。到殿前时,看到鼎里油正沸腾。两侧的武士用目光看着他,邓芝只是微微一笑。近臣把他引到帘子前,邓芝向吴王作了长揖,但没有拜。吴王命人卷起珠帘,大声喝道:“你怎么不拜!”邓芝昂然回答:“上国的使者,不拜小国的君主。”吴王大怒说:“你以为自己是什么人物,想用三寸之舌效仿郦生说齐吗!快进油鼎!”邓芝大笑着说:“人们都说东吴有很多贤人,谁会害怕一个书生!”吴王更生气了:“我怎么会怕你这样一个人?”邓芝说:“既然不怕邓伯苗,怎么会害怕你们呢?”吴王说:“你是想为诸葛亮当说客,来告诉我与魏国断交向蜀国求和,对吗?”邓芝说:“我只是蜀中的一个书生,特意来为吴国的利益而来。你们设兵设鼎,以拒绝一位使者,真是局量之小,容不下大事啊!”
吴王听后感到惭愧,立即命令武士退下,邀请邓芝上殿,给予他上宾的礼遇。吴王说:“先生的话,正合我心意。我现在想与蜀主联和,您能为我介绍吗?”邓芝说:“刚才想要烹杀小臣的,还是大王您;现在想要使小臣的,也是大王您。大王还是心存疑虑,怎么能让别人信任呢?”吴王说:“我已经决定了,请先生不要怀疑。”
于是吴王留住邓芝,召集许多官员问道:“我一个人掌管江南的八十一州,还有荆楚的地方,竟然比不上西蜀的偏僻地区。蜀地有邓芝,不会让他的主子丢脸;而吴国却没有一个人去蜀地,来表达我的想法。”这时,有个人站出来说:“我愿意去。”大家一看,是吴郡的一个人,姓张,名温,字惠恕,现在是中郎将。权说:“我担心你去蜀见到诸葛亮,无法传达我的心意。”温说:“孔明也是人,我有什么好怕的?”权大喜,重赏张温,让他和邓芝一起去四川通好。
话说孔明自从邓芝离开后,向后主奏道:“邓芝这次去,事情一定能成。吴地人才辈出,肯定会有人来答礼。陛下应该礼貌对待他们,让他们回去吴国,以便建立友好关系。如果吴国和好,魏国就不敢对蜀地用兵了。吴国和魏国如果都安定,我就可以征讨南方,平定蛮族,然后再考虑魏国。魏国削弱了,东吴也就不会长久存在,这样就可以恢复统一的基业了。”后主同意了。
没多久就收到东吴派张温和邓芝来川答礼的消息。后主召集文武百官在丹墀上,让邓芝和张温入殿。张温自以为得志,昂首阔步上殿,见后主施礼。后主赐给他锦绣的坐墩,坐在殿的左侧,设宴款待他。后主只是敬礼而已。宴会结束后,百官送张温到客舍。第二天,孔明设宴招待他。孔明对张温说:“先帝在世时与吴国不和,现在已去世。如今的主上,十分仰慕吴王,想要放下旧恨,永远结成友好关系,共同对抗魏国。希望大夫好好回奏。”张温领命而去。酒喝到一半,张温喜笑自如,显得有些傲慢。
第二天,后主将金帛赐给张温,在城南的邮亭设宴,命众官相送。孔明热情地劝酒。正喝酒的时候,忽然有一个人醉醺醺地走了进来,昂首长揖,入席就坐。张温很奇怪,就问孔明:“这是什么人?”孔明回答:“姓秦,名宓,字子勑,现在是益州的学士。”张温笑着说:“称作学士,不知道你心里学的是什么?”宓严肃地回答:“蜀中三尺的小孩,大家都在学习,何况我呢?”张温说:“那你说说你学的是什么?”宓回答:“上至天文,下至地理,三教九流,诸子百家,无所不通;古今兴衰,圣贤经典,无所不览。”张温笑着说:“你既然说得那么大,让来问问天的事:天有头吗?”宓说:“有头。”张温问:“头在什么地方?”宓说:“在西方。《诗》云:‘乃眷西顾。’所以头在西方。”张温又问:“天有耳吗?”宓回答:“天高而听低。《诗》云:‘鹤鸣九皋,声闻于天。’没有耳朵怎么能听?”张温又问:“天有脚吗?”宓说:“有脚。《诗》云:‘天步艰难。’没有脚怎么能走?”张温又问:“天有姓吗?”宓说:“怎么能没有姓!”张温问:“姓什么?”宓回答:“姓刘。”张温问:“你怎么知道?”宓说:“天子姓刘,所以我知道。”张温又问:“太阳是从东边升起的吗?”宓回答:“虽然是从东边升起,但却在西边落下。”
此时秦宓的语言清晰流畅,回答问题如行云流水,满座皆惊。张温无言以对,宓又问:“先生东吴的名士,既然问天的事,必然能深刻理解天的道理。以前混沌未分,阴阳未判;轻清的东西上浮形成天,重浊的东西下沉形成地;直到共工氏战败,头撞上不周山,天柱折断,地维缺失:天既然轻清而上浮,为什么会倾向西北呢?另外,我想知道轻清之外,还有什么其他的东西?希望先生教我。”张温无言以对,只好避席而谢说:“没想到蜀中人才辈出!恰巧听到你讲论,使我豁然开朗。”孔明担心张温会感到羞愧,因此用好话解围说:“席间问难,都是开玩笑罢了。您深知安邦定国的道理,何必在这里争论呢?”张温拜谢。孔明又让邓芝去吴国答礼,并与张温一起同行。张温和邓芝两人拜辞孔明,朝东吴的方向而去。
吴国的王看到张温进入蜀国还没有回来,就召集文武百官商议。突然有近臣奏报:“蜀国派邓芝和张温一起来国里答礼。”权于是召邓芝进来。张温在殿前拜见,称赞后主和孔明的德行,希望能永远结成联盟,特意派邓芝来答礼。权听后非常高兴,于是设宴款待他们。权问邓芝:“如果吴国和蜀国齐心合力消灭魏国,天下太平后,两个国家分治,这不是很好吗?”邓芝回答说:“天上不能有两个太阳,人民也不能有两个王。如果消灭魏国后,不知道天命归谁。作为君主的,应该修身养德;作为臣子的,应该尽心尽力。这样战争就会结束。”权大笑说:“你的诚意果然如此啊!”于是厚重赠送给邓芝,让他回蜀国。从此吴国和蜀国开始交好。
魏国的间谍得知了这个消息,迅速报告给中原的魏主曹丕。曹丕听后非常生气,说:“吴国和蜀国联手,必然有侵略中原的意图。我们应该先出兵攻打他们。”于是大规模召集文武百官商议出兵的事。此时,魏国的大司马曹仁和太尉贾诩已经去世。侍中辛毗站出来说:“中原的土地广阔而人口稀少,想要用兵未必能见到好处。如今的计划,不如养兵屯田十年,积累足够的粮食和兵力,再出兵,这样才能打败吴国和蜀国。”曹丕怒道:“这是迂腐的说法!现在吴国和蜀国已经联手,早晚会来侵犯我们的领土,何必等十年!”于是下令出兵攻打吴国。司马懿奏道:“吴国有长江的险阻,只有船才能渡过。陛下亲自出征,可以选择大小战船,从蔡、颖出淮,攻取寿春,到广陵,再渡江直取南徐:这是上策。”曹丕听从了他的建议。于是日夜加紧造船,造了十只龙舟,每只长二十余丈,可以容纳二千多人,还准备了三千多只战船。在魏国黄初五年秋八月,聚集了大小将士,命曹真为前部,张辽、张郃、文聘、徐晃等为大将先行,许褚、吕虔为中军护卫,曹休为后方,刘晔、蒋济为参谋官。前后水陆军马三十余万,于是出发。封司马懿为尚书仆射,留在许昌,凡国政大事,皆听从司马懿的决断。
不说魏兵起程。此时东吴的间谍探知了此事,报告给吴国。近臣慌忙向吴王奏报:“如今魏王曹丕,亲自乘坐龙舟,带着三十多万水陆大军,从蔡、颖出淮,必定要去广陵渡江,进攻江南,后果非常严重。”孙权大惊,于是召集文武百官商议。顾雍说:“如今主上已经与西蜀联好,可以修书给诸葛孔明,令他出兵汉中,以分散敌人的力量;同时派一位大将,驻兵南徐来抵挡他们。”权说:“非陆伯不可担此重任。”雍说:“陆伯现在镇守荆州,不可轻动。”权说:“我不是不知,只是眼前没有合适的人。”话还没说完,一个人从班上走出来说:“我虽然能力不足,但愿意统一军队对抗魏兵。如果曹丕亲自渡江,我一定要抓住他献给您;如果不渡江,我也能杀掉魏兵大半,现在魏兵不敢正视东吴。”权一看,原来是徐盛。权大喜说:“如果能让你守住江南一带,我还有什么好担心的!”于是封徐盛为安东将军,统领守卫建业和南徐的军队。盛谢恩,领命而退;随即传令给众官军多准备器械,多设立旗帜,以便守护江岸。
忽然一个人站出来说:“今天大王将重任委托给将军,想要打败魏兵并抓住曹丕,将军为何不早点出军渡江,去淮南迎敌?要是等到曹丕的军队来了,恐怕就来不及了。”盛一看,原来是吴王的侄孙韶。韶字公礼,官职是扬威将军,曾在广陵守卫;年纪轻轻但很有胆量。盛说:“曹丕势大,而且还有名将为先锋,不可渡江迎敌。等他们的船都聚集在北岸,我自有办法来对付他们。”韶说:“我手下有三千军马,而且熟悉广陵的地形,我愿意亲自去江北,与曹丕决一死战。如果不胜,愿意接受军令。”盛不肯同意。韶坚持要去,盛却不肯,韶一再请求出征。盛怒道:“你如此不听命令,我如何能指挥其他将领?”于是命令武士把韶推出去斩了。刀斧手把孙韶带到营外,立起皂旗。韶的部将飞快地报信给孙权。权听后,急忙上马来救。武士正准备行刑,孙权及时赶到,喝散刀斧手,救了孙韶。韶哭着奏报:“我以前在广陵,深知地利;若不在那里与曹丕拼杀,等他渡过长江,东吴就要完了!”权直接走入军营。
徐盛迎接进帐,报告说:“大王命我担任都督,带兵抵抗魏国;现在扬威将军孙韶不遵守军法,违令应该斩首,大王为什么宽恕他?”权回答说:“韶年轻气盛,误犯军法,我希望能够宽恕他。”盛说:“法律不是我制定的,也不是大王制定的,而是国家的法律。如果因为亲近而免除他的罪责,那怎么能让大家服从呢?”权说:“韶犯法,本该由将军来处理;可是这个孩子虽然姓俞,但我兄弟非常疼爱他,给他赐姓孙;他对我也有贡献。如果现在杀了他,就辜负了兄弟情义。”盛说:“我看在大王的面子上,给他一个死罪。”权于是让孙韶拜谢。韶不肯拜,厉声说:“我认为,只要带军去打败曹丕!即使死也不服你的见解!”徐盛面色大变。权斥退孙韶,对徐盛说:“就算没有这个孩子,对军队有什么损失?今后不要再用他。”说完就回去了。那天晚上,有人报告徐盛说:“孙韶带着本部三千精兵,偷偷渡江去了。”盛担心会出问题,在吴王面前不好交代,于是叫丁奉出个密计,带三千兵渡江去接应。
与此同时,魏主驾着龙舟到了广陵,前面曹真已经带兵列在大江岸边。曹丕问:“江岸上有多少兵?”真回答:“隔着岸远望,根本看不见一个人,也没有旗帜和营寨。”丕说:“这必然是计谋。我自己过去看看真相。”于是大开江道,放龙舟直接到大江,停在江岸。船上插上五色的龙凤日月旌旗,仪仗簇拥,光辉耀眼。曹丕坐在船中,远望江南,看不见一个人,回头问刘晔和蒋济:“可以渡江吗?”晔说:“兵法讲究虚实相生。他们见到大军来了,怎么会不准备?陛下不能急切。还是等三五天,观察他们的动静,然后派先锋渡江去探探情况。”丕说:“你的话正合我意。”
这天晚上,宿在江中。夜里月黑,军士们都拿着灯火,照得天地明亮,像白天一样。遥望江南,根本看不见一点火光。丕问左右:“这是为什么?”近臣回答:“听说陛下的军队来了,所以大家都逃跑了。”丕暗自笑。等到天亮,浓雾弥漫,前面看不见。过了一会儿风起,雾散云收,望见江南一带都是连绵的城池:城楼上枪刀闪耀,遍城插满了旌旗。没过多久,几个人来报告:“南徐沿江一带,直到石头城,连绵数百里,城郭舟车,接连不断,昨夜建成。”曹丕大吃一惊。原来徐盛用芦苇绑成假人,穿上青衣,举着旌旗,站在假城的楼上。魏兵看到城上许多人,怎么能不怕呢?丕叹息道:“魏国虽然有千军万马,却没有办法使用。江南的人物如此,不可轻易想图!”
正惊讶的时候,突然狂风大作,白浪滔天,江水溅湿了龙袍,大船快要翻了。曹真慌忙让文聘撑小舟急来救驾。龙舟上的人都站不住。文聘跳上龙舟,背着曹丕下到小舟,急奔入河港。忽然有流星马报道:“赵云带着兵从阳平关出,直取长安。”丕听了,大惊失色,立刻命令回军。众军各自奔走。后面吴兵追上来了。丕传旨让大家尽弃御用之物而逃。龙舟快要进入淮河,忽然鼓角齐鸣,喊声震天,斜里冲出一支军队:为首的将领正是孙韶。魏兵抵挡不住,折损大半,淹死的人无数。诸将拼命救出魏主。魏主渡过淮河,不到三十里,淮河中一带的芦苇,预先灌了鱼油,全部着火;顺风而下,风势很猛,火焰冲天,封住了龙舟。丕大惊,急忙下小船靠岸时,龙舟已经着火了。丕慌忙上马。岸上又冲来一支军队;为首的将领正是丁奉。张辽急忙骑马来迎,被奉一箭射中腰部,却得徐晃救了,保护魏主逃走,折损军队无数。后面的孙韶、丁奉夺得马匹、车仗、船只、器械不计其数。魏兵大败而回。吴将徐盛获得了大功,吴王加以重赏。张辽回到许昌,箭伤破裂而死,曹丕厚葬他,没什么好说的。
赵云带领军队从阳平关杀出来时,突然收到丞相的消息,说益州的一个官员雍闿与蛮王孟获结成联盟,发动了十万蛮兵,侵扰四个郡。于是,赵云决定回军,命令马超坚守阳平关,丞相打算自己南征。赵云于是急忙收兵返回。这时,孔明在成都整顿军队,亲自准备南征。正是:
方见东吴敌北魏,又看西蜀战南蛮。
不知道胜负如何,且看下文分解。
如果觉得内容不错,欢迎你点一下「在看」,或是将文章分享给其他有需要的人^^
相关好文推荐: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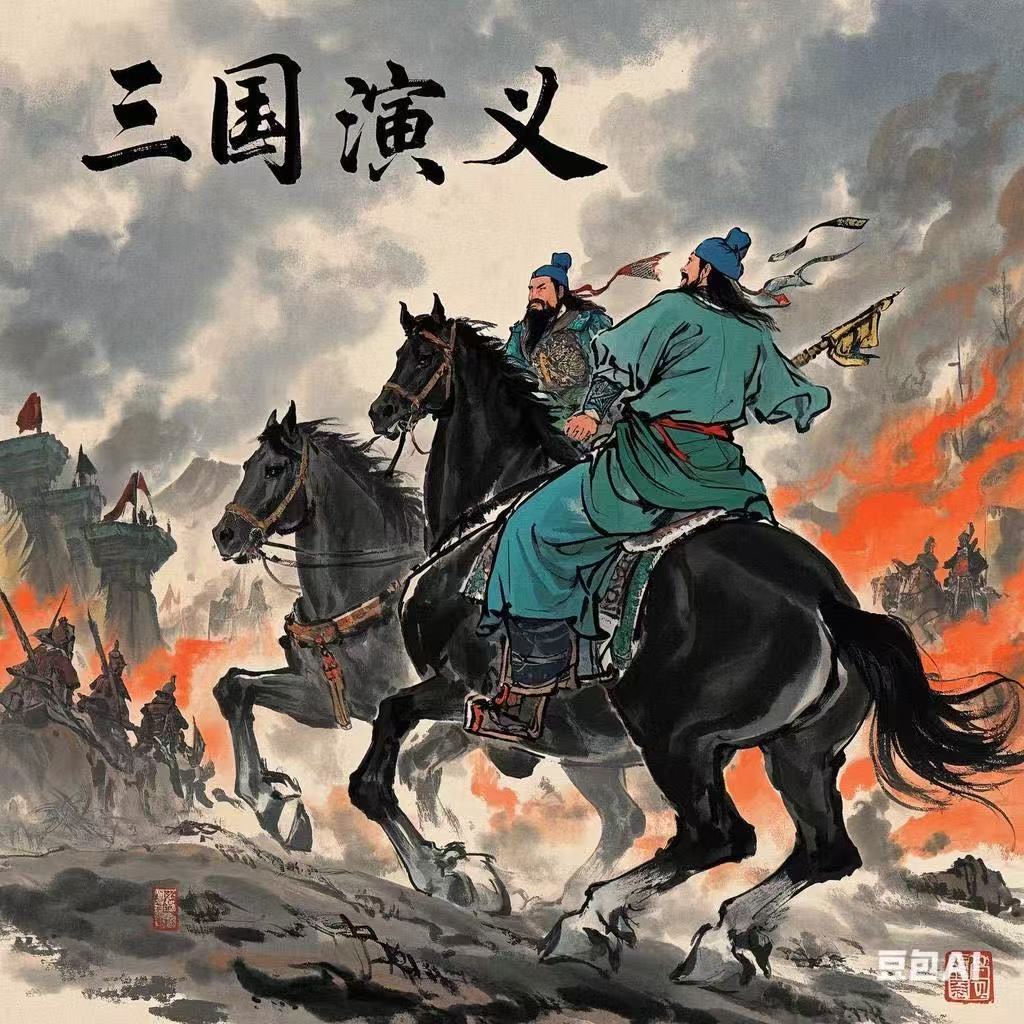
0条留言